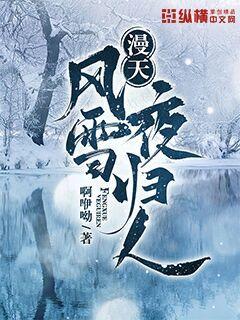漫漫千载,玄微子确实见过一些惊才绝艳的天才,修炼三五年就能连破五境,直上宗师上境,但要勘破逍遥境的大门槛,却绝非易事,许多所谓的天才就是前五境顺风顺水,一路领先同龄人,但因为基础不牢,在进入逍遥境的门槛边上徘徊了许多年。只有真正跨过了这道修行路上的绝大关隘,才算得上天才。当然自家少爷那种就属于天才中的天才,天才二字都难以形容的大天才,离家之时只是宗师上境,十年间未进一步,但最终一朝连破三境,不但打破了从宗师三境迈入逍遥境的大门槛,还一鼓作气,直上逍遥上境的巅峰。
不过眼前梅夏这个小子也绝对算得上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了,半个月前上山之时,看他气息平平,与凡夫俗子并不差别,当是还未开始修行,就在进入幻境的这两天,走走停停,看山看水看风景,就在睡梦里走了别人半辈子才能走完的路,两天破六境,以后有无来者不知道,但绝对是前无古人的。不过这倒是更加印证了玄微子的猜测,这小子一定和少爷有着很深的联系,因而在少爷留下的“幻境”中获得了很多的馈赠。
当然即便如此,也不得不说梅夏算得上天赋异禀,天生与天道自然亲近,因而对于大道的领悟也更加敏锐。
玄微子神念一动,两人出现在一棵有着硕大树冠的枯桑树下,天风猎猎,吹得树枝吱吱作响,古人有诗云,“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可算体物细致,比兴委婉。梅夏心中感叹那棵桑树的古老和硕大,闭上眼睛,似乎能够想见那棵古老桑树曾经枝繁叶茂的样子,细密的绿叶在风中摇摆,那一阵阵树叶的起伏便仿佛海上粼粼而起的波浪,感知和传达着风的力量。
玄微子就立在梅夏身旁,抚须微微而笑,这便是天赋了。古人有望一叶而知天下秋,而能从枯桑想象到绿叶挂满枝头的活桑,这便是灵性和悟性了。写出那句“枯桑知天风”的人,玄微子见过,是道门里相当不错的后辈,修道天赋不见多么惊人,写诗作文却是一代风流,风格偏向诡奇,有“秋坟鬼唱”的称誉。
天道便如这天风,寻常人如何能看见摸着,不过是借万物在风中如何起伏摇摆,来感知天风,窥视天道。
神梦山中,年来年去,春往春还,花开花落。明月年年春来,便喜欢在这山中坐着,看着眼前纷纷扬扬落下的桃花发呆。明月心里很是郁闷,那个来寺里住了半月就走了的小胖子,着实过分,当初说一去三四天就会回来,从那天算起,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年了。
不过明月有一样好,就是没心没肺,不记仇,也无隔夜之恨,不回来就不回来吧,日子一天天也就那么过去。当年古灵精怪的小丫头,如今已经渐渐出落的眉眼如画,若是着一身淡红粉裙,手捻一枝桃花,不知可让多少少年辗转反侧,去吟唱那句“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而和明月从小朝夕相对,可以说青梅竹马的清风,个子窜的极快,明月现在都只能到他肩膀了,如今也长成一个皮肤白皙、气度淡泊从容的翩翩少年,皎然如玉树临于风前。尤其是再一笑,就更如春风拂面,看的明月老是觉得脸上发烧。而且,听说师兄再过几个月就可以说话了,那时就是逍遥境的厉害仙师了。
所以明月最近就很开心,有事没事也总喜欢在山里疯跑,隔三差五也会下山去附近的一个小镇。两年前,有位看上去很好看的妇人上山拜寺,明月看师父鲁山海苦着脸,就主动去开门,那妇人一见自己就开心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乖,叫师娘!”熟络热情得让明月都招架不住,进门之后,独自拎着许多鸡鱼生鲜,就要一头往厨房里钻,嚷嚷着说要明月尝尝师娘的手艺。
后来这位天上掉下来的“师娘”就给明月讲了讲,捡一些陈年旧事说了说,无非是当年怎样被你师父的不羁风采迷住了,可你师父这人吧,看着五大三粗,是个爽利人,可谁知竟然还会害羞。听得明月一愣一愣的,没想到师父年轻时还能有迷妹,而且还是这么好看的,于是明月就跟着一通埋怨,说师父当年一定是眼神不好使,不然师娘这么美的大美人,不会那么轻易放过的。两人一起给鲁山海一顿数落,关系好的仿佛失散多年的姐妹,无话不说。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也根本没有鲁山海能见缝插针、自辩清白的空当,草草就被定下了辜负佳人的罪名。
打那以后,明月就时常下山去小镇上一间吃食铺子,师娘就住在那里。师娘便嘱咐她多去陪陪师娘说说话,你师父那呆子是个不解风情的主儿,也就你比较有良心,是师娘的贴身小棉袄。
清源小镇实际上并不算是严格意义的江南小镇,因为地处南北交界偏南一点,相较于仍在东南千余里的神梦山来说,春意便来得慢一些,晚一些。尽管前人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佳句,海拔的高低确会影响春天的迟与早,却也并不能改变南北相差千里所带来的气候差异。因而此时,清源小镇里春寒尚且料峭,河冻未解,岸边的垂柳只是远远看去有一丝浅浅的绿意,近看却忽然消失不见。
刚下了学正打算离开学塾的丹青,突然听见有人在唤自己的名字,抬头一看,是黎老先生,正笑着向自己招手。
“来来,端木先生来信了,这封是给你的”,说着便递来一封信。
丹青双手接过,向先生鞠了一躬,“先生明天见!”
丹青走后,黎老先生长叹一声,“哎,这么多年真是苦了这孩子了。”
学塾角落里一个大约十三四岁的少年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回过神来,见陈丹青已经走出了学塾,于是收拾好书桌,便快步跟了出去。
“别来数载,光阴匆匆,师父一切皆好,唯北地春晚,此时尚冰封千里,不及南方,柳枝袅袅,春水悠悠,扫花温酒,固春日之乐事。前人诗云,‘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心神往之。顾念昔日,每临书而叹,辍笔而伤,不知庭前桃李,今开几许?阶下春风,拂谁之面?书声琅琅,何人闻听?又不知如花丹青,迷倒几家少年……”
“师父这老不正经的!”丹青回到家一边看信一边忍不住笑,吐槽了一句,又继续看信,看到“丹青可问及父母,若得父母应允,可女扮男装,来北地一游,行路万里,则可以言学矣。”思及父母,丹青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不过还是坚强地没有哭出来,抽了抽鼻子,继续往下读。
“可多留意,书中字里行间,朱笔旁注,勤修诚意正心学问,小可以涵养身心,中可以练气凝神,大可以寻绎大道,切记切记。”
丹青平日也听到学塾里一些男孩谈论江湖事,说起修行之人的传闻,什么北方儒家每位三十六书院院长都是天下间数一数二的武学大宗师,文武从来不分家。丹青想师父留下的那本诗经注解中的一些旁注想必就是这些武学修行的东西了。她以前翻书偶尔留意,也并未深思,只当是寻常书批。她当然很想开始修行,这样面对一些猝然降临的危险,也有一定的自保之力,将来也可以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游历天下,去找父母和弟弟。嗯,丹青心中下定决心,要好好修行,不怕吃苦。巴掌大的脸上满是可爱的倔强,以及那稚嫩的倔强中透出的一点坚毅。
正在此时,大门半开,探出一个脑袋,看见丹青正低头读信,熟门熟路地进来,轻轻关上门,蹑手蹑脚,正准备去劈柴,听见一声清冷的嗓音传来,“郝仁,我说了,不需要你帮,我自己能做这些。”来者是和丹青同上学塾的同窗,虽然看上去呆头呆脑的,但听说是小镇南边一家鼎鼎大名的酒楼老板的独子。
丹青独自一人生活了三年,如今已经十三岁了。平时都穿着学塾统一制式的灰白衣服,混在一屋子学子中间,确实不太明显。但去年因为小巷里的张婶给自己做了一身新衣裳,下身是一条浅绿色的罗裙,还非要丹青穿着去上学,丹青无奈。到了学塾,就看呆了一众学子,大家这才发现原来以前那个不太跟人玩耍、时常自己闷在桌前看书的小姑娘,已经不知不觉变成一个透露着些许青春魅力的大姑娘了。
小镇民风淳朴,又兼此处是学塾,倒并无市井间的轻薄寻芳浪子,只是一些同窗渐渐盯着她看,背后也时时议论着。学塾里也有几个跟丹青同龄的姑娘,告诉丹青,“别人盯着你看,你就大大方方地让他们看去,咱们女学生也有花痴的时候呢!”丹青觉得有理,只是第二天就又换回了以前灰白单调的衣服,因为好衣服要在重要的日子再穿,平时穿得那般总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但有时麻烦往往会自己找上门来,一天傍晚,丹青走在福禄街上,就碰见几个嬉皮笑脸的混混,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正巧就被那郝仁碰上了,他便要见义勇为,结果被打了一顿,那些混混见事情闹得有些不可收拾,就匆忙溜了。丹青感激地冲他说,“你是个好人!”
丹青待人接物当然谈不上不恭敬,只是往往也敬而远之,好似身边一切都与她关系不大,她既不参与,也不贸然发些议论,在人群中便显得格格不入起来。但经过此事后对同窗郝仁便稍微温和了一点。只是,这点温和并不足以打消其清冷的态度,不拒人于千里,却也有五百里。
郝仁听见丹青不让他劈柴,便讪讪地想去厨房提桶,要去巷子深处的一口古井里打水。丹青无可奈何,便将手中的信小心收好起身去劈柴。僻静的小院里,落日余晖点点。可岁月如此,并不静好,那只是波涛下面压抑的平静。